
香港的密度,總是令人嘆為觀止。
高聳入雲的樓宇自不必說,縱深之處還有數不盡的林立密布的屋邨。

不知什麼時候,屋邨成了懷舊的代名詞,和粵語歌、港產片一樣,凝固在20世紀記憶中的香港裏。
近些年,屋邨除了承擔都市人懷舊的功能,還是新晉網紅打卡聖地。逛膩了商超,去公屋拍照,成了香港旅遊的小眾路線。
在很多人眼中,香港是中環的人擠人,維港的霓虹,蘭桂坊的夜,目之所及的繁華。
但對於很多老香港而言,香港也像是「天水圍的日與夜」,比城市叢林慢一拍的深水埗,屋邨的一條街一幢樓。

邨屋,不僅是滿足生存需求的住所,更是建築美學的典範。
對於空間奇缺的香港而言,排列五花八門的屋邨,作為設計元素被壓縮在咫尺之間,是再好不過的圖形語言。
H字、I字、Y字、井字等不同樓型排列組合,外牆顏色和圖案的繽紛搭配,幾百個窗戶密集整齊的大廈立面,邨屋極盡點、線、面視覺美學之能事,令人忍不住按下快門。

赤橙黃綠青藍紫,萬丈光芒彩虹邨。
近些年大熱的彩虹邨,如它的名字有著絢爛的色彩。不少人在它獨特的外牆下,留下獨一無二的照片。還有仿佛用彩色蠟筆勾畫出來的籃球場,明亮的色彩足令壞心情掃地。
彩虹邨內部的大樓和道路均以彩虹七色作為首字,其獨特的外形設計還獲得了1965年香港建築師學會銀牌獎。
南山邨彩虹橋也常引來打卡風潮,下雨過後再去,還能看見美麗的「屋邨之境」。落過雨的水面,忍不住想拍下留下熱愛這裏一切的身影。

勵德邨是全港唯一一座圓環式建築,四幢醒目的大樓以連廊相接,內部環形層層疊疊,在中庭仰望,像掉進時空隧道。站在高處,可以俯瞰銅鑼灣,甚至看到片段維港。
「怪獸大廈」比較特別,五棟大廈拼成巨大的E字形,處處都在反映舊香港人多地少的民情,是一組「舊到發霉」、「密集如森林」、「房齡近50年」的組合民居建築群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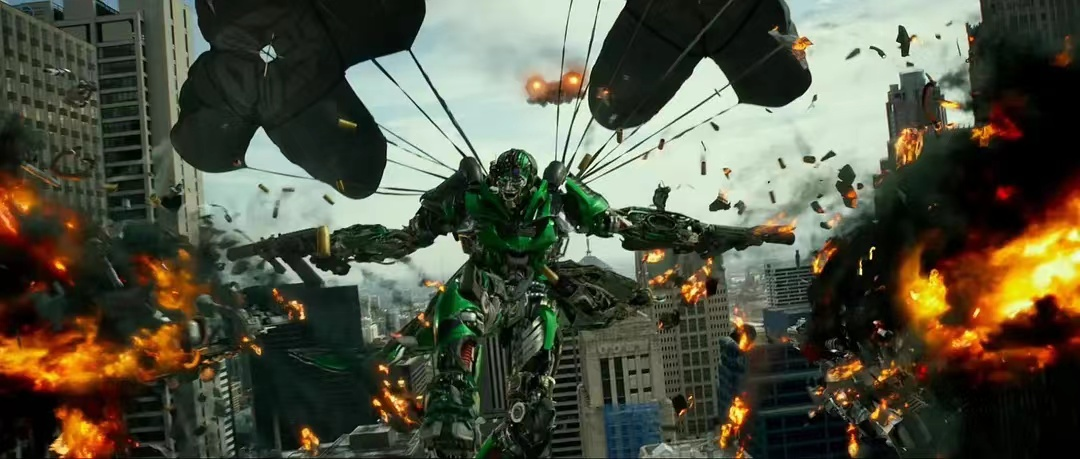
《變形金剛4》劇照
《變形金剛4》曾來這裏取景,《攻殼機動隊》《雲圖》《銀翼殺手2049》的靈感,也來自於此。賽博朋克不是繁華的外衣,最發達的城市,配上混亂崩壞的社會,恰好符合賽博朋克式的科學幻想。
不同於彩虹邨歲月靜好的感覺,這棟大廈有如怪獸般宏偉神秘的觀感。大廈三面合圍,和後修剪的住宅合圍成天井。
為了盡可能的裝下更多人,屋邨的建築風格大多密集擁擠,從高樓下瞰,人行如蟻過,萬窗像蜂巢。可住逾萬人,相當於一個歐洲小國的全國人口數量。香港建築師絞盡腦汁,設計出充滿美感的幾何設計和規則的布局,很難不懷疑建築師們不是處女座。
形形色色、奇形怪狀的屋邨,成為香港這座大城市神奇的存在,像是一個巨大的萬花筒,裝著幾千戶人家色彩斑斕的夢。

穿越近百年的屋邨經過時間的發酵,無形中衍生出香港特有的屋邨文化。
長長的走廊、門戶相對的間隔,以及不設防的鐵閘、知根知底的鄰里,都是舊式公屋獨有的特色。
屋邨空間有限,每一寸空間都被利用到極致,每一家窗戶都開得老大,因為只有那一面能夠讓陽光灑進屋裏。小小的密密麻麻的陽臺,魚乾臘肉、各種雜物卻被擺得滿滿當當,儼然一個繽紛晾曬場。

香港的屋邨裏,有著撫慰人心的人情。
當人們懷舊的時候,就會想起屋邨。許多屋邨,承載著老人們的一生,他們自搬進來,就與院子裏的樹木一起長大。
從孩提時期走過來,時間流轉,很多東西消失了,而屋邨的圍欄圍住舊時光,可以讓他們回想不在的人和事。
「我們的成長過程中有很多符號,那些符號可能跟我們整個人的生活、很多走過的路有緊密聯繫,但這些符號消失了。譬如聽歌,我們都喜歡張國榮、喜歡Beyond、陳百強、梅艷芳,這些人全都不在了,但我們還在。我們追捧他們的時代就是公屋的時代,所以東西都是緊扣著,讓我們可以回想已經不在的人。」在《我們都是這樣在屋邨長大的》一書的序中,作者之一范永聰這樣寫道。
屋邨的生活,留存著些古樸的人情。
公屋裏的人家,大多敞開著門,在鐵閘中間遮一塊布,既是為了通風,也是保護私隱。夏天經過走廊時簡單一瞥,每家每戶露出的都是腦袋和腳,大蒲扇不時晃蕩。
邨內隨處可見香港七八十年代淳樸的街坊生活。在球場上晾衫的婦女、坐在椅子上的老人、放學後拍著籃球回家的學生、麵包鋪早晨的繁盛、熟食檔消夜的熱鬧。冰室、雜貨店、士多店等還是老樣子,他們與古老的建築一起,形成一座城市的文化符號。

窄小的屋邨,幾十戶人家共享一條走廊,也因這侷促的空間,人與人之間有了交集與交心。鄰里開飯了,自然而然會問來不來吃飯,交換飯菜是常態。人們來自五湖四海,偏愛菜系各有不同,所以屋邨仔的胃,不誇張的說是嘗遍整個中國。
各家的孩子自幼打成一片,少年情誼大過天,在球場打球踢波的,一起玩過跳房子的,放學後在天臺一塊看日落的,很難說不是同一幫人。一句「我們是同個屋邨長大的」,就是最強的友情註腳。

數不清的康樂設施,小到滑滑梯、蹺蹺板、老人友好的踏步機,大到籃球場,聚攏了一個社區最多的人氣。到了晚上,老中青們都從二十來平米的洞裏鑽出來,一片片的嬉鬧聲由這裏傳開。老人們以緩慢的步伐緩慢散著步,他們身上那股經歷了大半輩子的煙火氣,在孩童嬉鬧聲的沾染里,在某一個不知名的頻率里共振。
「哪怕是當年的確令人覺得困擾的生活細節:整棟樓冷氣機太多電力不堪負荷夜半大停電啦、隔音效果太差住得太密導致鄰居家的吵架聲一聽無遺啦、食肆太過分散極其偶爾才能吃到喜歡的食物啦、小販挨家挨戶兜售產品啦……回想之時,竟也令人「恨」中帶笑。」 范永聰寫道。

沙田瀝源邨
有人說,大篇幅的渲染屋邨的人文情懷,是因為住不起私人住宅而發酸嗎?誠然,沒有人不追求舒適的居住環境,而人們偏愛屋邨,是有跡可循的。
在屋邨最多最鼎盛的時期,有超過200萬人口住公屋,已然成為一代人成長的集體記憶。
從屋邨出來的,不乏草根明星。顯徑邨的吳卓羲、大興邨的鄧麗欣、恆安邨的容祖兒、王祖藍、楊怡、還有大名鼎鼎的導演吳宇森。吳宇森導演曾經在回憶錄中提及屋邨:
「在這裏,我曾經送過外賣,送米上七樓,做過臨時演員,在樓梯底賣提子乾,我竟然餓得吃了一大半。在這裏,我夜間睡在公用走廊的帆布床上看星,發著電影夢,日間渴望聽到附近教堂的鐘聲,有過很多的生活磨鍊,讓我透徹感受人間悲喜,左鄰右舍的溫馨和濃濃的人情味。天空有時灰濛,很多時候感到悶熱,但感覺人生還是溫暖的。」
在搬遷頻繁的現代社會,習慣了「老死不相往來」的人類,不免會被這一方氤氳的煙火所著迷。

香港填海百年,維港兩岸高樓拔地而起,成就了亞洲的金融中心、全球最自由經濟體、中國人均GDP第一城。這是香港人創造出的奇蹟。

而寸土寸金也意味著,樓價只有更高沒有最高,地多人少的原因,不僅是人海人海,更是樓山樓海。
1841年,獅子山腳下建立了一座要塞——九龍城寨,時代更迭,城寨成了三不管的法外之地。
1945年,香港不過65萬人,隨著移民潮到來,1970年,全港人口已至400萬。這裏令密集恐懼癥發作的高樓,不過香港人口暴增的縮影。
也是上世紀中葉,寮屋區開始出現,很多單位被分拆成板間房或上下格床出租,於九龍北部搭建臨時落腳的木屋便是其中一處聚居地。

早期的寮屋簡陋,多是市區邊緣的農地,缺乏基本生活設施,只有非常簡陋的烹飪和照明工具。寮屋多以用木材搭建,區中夾雜著不少小型工廠,工廠裏可能存有易燃的物體,寮屋區火災成為當時的普遍現象。
公屋誕生緣起於一次災難。1953年12月24日聖誕夜,九龍石硤尾公屋發生的一場大火,令5.3萬居民無家可歸,香港政府在原址附近興建廉租屋邨並成立香港屋宇建設委員會。
此後,由香港屋宇建設委員會興建的首個廉租屋邨——北角邨在1957年落成。
公屋,又稱屋邨,多形成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,是香港公共房屋最常見的類別,由政府或志願團體興建,出租給低收入市民,是香港絕大多數基層人士的家。
自上個世紀50年代起的公屋政策,養活著一大批香港本土平民,一個城市生活的基本形態,在這裏都能找到。

許是1953年的石硤尾大火太過令人震撼,提起香港最早期的公屋,人們很自然會聯想起造價低廉、環境惡劣、不求住得好,但求塞得滿的沙丁魚罐頭式徙置區。
在公屋發展的早期階段,政府已經有了較為長遠的目光,公共屋邨從屋開始慢慢發展成了邨。
「邨」,字面意思是一群人屯居在一起的社區,區別傳統意義的「村」。它除了是滿足人的生存需求的住所外,更是集合各種街市、康樂設施和休憩空間的小型社區。

香港的西環邨,公共空間寬闊,樹木蔥蘢,環境通透,生存之外也兼顧了生活。這裏有獨立廚廁,有合理的人均居住面積,以比徙置屋邨稍高但仍可負擔的租金,供給收入較好的白領階層申請。
香港人夢寐以求解決的居住問題,似乎在此能得到啟發。
《西環邨——風雨不動安如山》中,兩位在西環邨服務多年的資深社工卻提出,原來除了降低質量只求安頓草根階層的徙置思維外,當年還平行地存在著一條重視空間布局和生活水平的房屋政策路線,1958年落成的西環邨正是這套理念的結晶。
屹立在堅尼地城的西環邨,倚山而建,已經走過六十年的風雨,就像是時空的交叉路口,一條街一幢樓,都帶著舊日香港的韻味。
「在世間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,屋村你住哪一座?」
香港是一座大城市,也是一座普通的城市。
不管怎樣,每座大城市,都有小人物在生活著。

車水馬龍的街道放大了孤獨,高聳入雲的大樓讓人產生疏離感,而老舊的屋邨,有最接近生活的樣子。住進了屋邨,就是住進煙火氣裏。
作為一個政府最小化,社會最大化的城市,香港精神,就是用最少的稅收,為市民提供最好的服務。
正如《西環邨——風雨不動安如山》作者在書中末尾所期待的那樣,「但願天下人都能安身在風雨不動的家,前路漫漫,安然無恙。」
(圖片除說明外,均來自網絡)
撰稿:羅維維
封面:楊亮
校對:卓玲
審核:雨杉 靜文




